
青燈黃卷,往往被作為學(xué)者讀書生活和學(xué)術(shù)實踐的常態(tài)象征。我們最初走上史學(xué)研究的道路時,導(dǎo)師林劍鳴教授就教示道:“前四史”和《資治通鑒》是首先必須通讀的,并且要求做細(xì)致的筆記。記得讀《資治通鑒》時,導(dǎo)師曾經(jīng)指示我們做核正日期記述的作業(yè)。我后來給吳玉貴《資治通鑒疑年錄》寫書評時,補寫了當(dāng)時作業(yè)中的內(nèi)容。以后曾承蕭兵、葉舒憲囑,做《史記的文化發(fā)掘》,書稿的底本主要是當(dāng)時通讀《史記》的筆記。
歷史學(xué)人的功夫并非全在筆墨之間,還有更廣闊的學(xué)術(shù)空間,更生動的學(xué)術(shù)體會。學(xué)問不僅在于書卷,也在于山野,在于塵泥。

因為本科學(xué)的是考古專業(yè),比較重視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的結(jié)合。這就是王國維倡導(dǎo)的“二重證據(jù)法”。后來又有學(xué)者提出“三重證據(jù)法”“四重證據(jù)法”,強調(diào)史籍和其他如考古文物信息、民族調(diào)查收獲以及圖像學(xué)資料的配合。
遵循史念海先生開辟的學(xué)術(shù)路徑,進行實地考察,是我曾經(jīng)從事研究戰(zhàn)國秦漢交通史取得一些新知的重要條件。除了讀書時集體考察、實習(xí)之外,第一次自主確定路線、計劃的野外考察,是為寫作碩士學(xué)位論文《論秦漢陸路運輸》,而于1984年4月成行的西安至商南古武關(guān)道。以自行車騎行方式走藍橋河、丹江路線,途中注意到藍橋河棧道遺跡,發(fā)表了《古武關(guān)道棧道遺跡調(diào)查簡報》(王子今、焦南峰合署,《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2期)。
當(dāng)時看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標(biāo)示戰(zhàn)國秦漢武關(guān)的位置,似在今丹鳳竹林關(guān)附近。經(jīng)實地調(diào)查,可知這一判斷應(yīng)予修正。由譚圖顯示唐以后武關(guān)的地點,發(fā)現(xiàn)“武”字陶文漢瓦以及漢“武候”瓦當(dāng),可以推定戰(zhàn)國秦漢的武關(guān)已經(jīng)在這里。相關(guān)認(rèn)識形成文章,多年后才發(fā)表,即《“武候”瓦當(dāng)與戰(zhàn)國秦漢武關(guān)道交通》(《文博》2013年第6期),《武關(guān)·武候·武關(guān)候:論戰(zhàn)國秦漢武關(guān)位置與武關(guān)道走向》(《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8年第1期)。1984年考察的收獲,還包括在當(dāng)?shù)匚奈锔刹恐敢聦ι眺狈獾氐拇_認(rèn)(王子今、周蘇平、焦南峰:《陜西丹鳳商邑遺址》,《考古》1989年第7期)。
后來,我們又以騎自行車的考察方式走子午道,在石羊關(guān)附近發(fā)現(xiàn)了非常漂亮的棧道遺存(王子今、周蘇平:《子午道秦嶺北段棧道遺跡調(diào)查簡報》,《文博》1987年第4期)。以后得到的有關(guān)“直道—子午嶺”和“子午道—直河”彼此南北對應(yīng)關(guān)系的認(rèn)識,和這樣的實地行走經(jīng)歷有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后來回憶,我還曾經(jīng)發(fā)表過一篇寫三國故事的歷史小說《子午云煙》(《延河》1986年第12期),也是以子午道交通為背景的。
考察灙駱道是與張在明、秦建明、周蘇平同行,根據(jù)道路通行狀況采用步行和騎摩托車交替的方式。我和周蘇平夜行嶺上,可能由于地圖識讀的差誤,沒有迎上另兩位同伴騎車接應(yīng),不得不停宿在一位老者的柴棚中。
古道通行的許多路徑,并非全是文化荒野。在位于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分水嶺附近的牧護關(guān)一帶,村民們都熟悉的韓愈詩句“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guān)馬不前”,會使你聯(lián)想到大嶺層云之間古人的行跡和心跡。在古富水驛遺址附近,你不僅可以看到大面積的秦磚漢瓦堆積以及村民修建廁所豬圈使用的漢畫像磚,還能夠得知當(dāng)?shù)厝藗儗τ凇案凰A”原名“陽城驛”故事的熟悉。武關(guān)道沿途有很多普通人不僅會吟誦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等詩句,也熟知元稹、白居易驛壁題詩實現(xiàn)情感交流的故事。而嚴(yán)耕望、李之勤等學(xué)者都曾經(jīng)通過唐詩記憶,復(fù)原驛路走向和驛館設(shè)置,發(fā)表過精彩的考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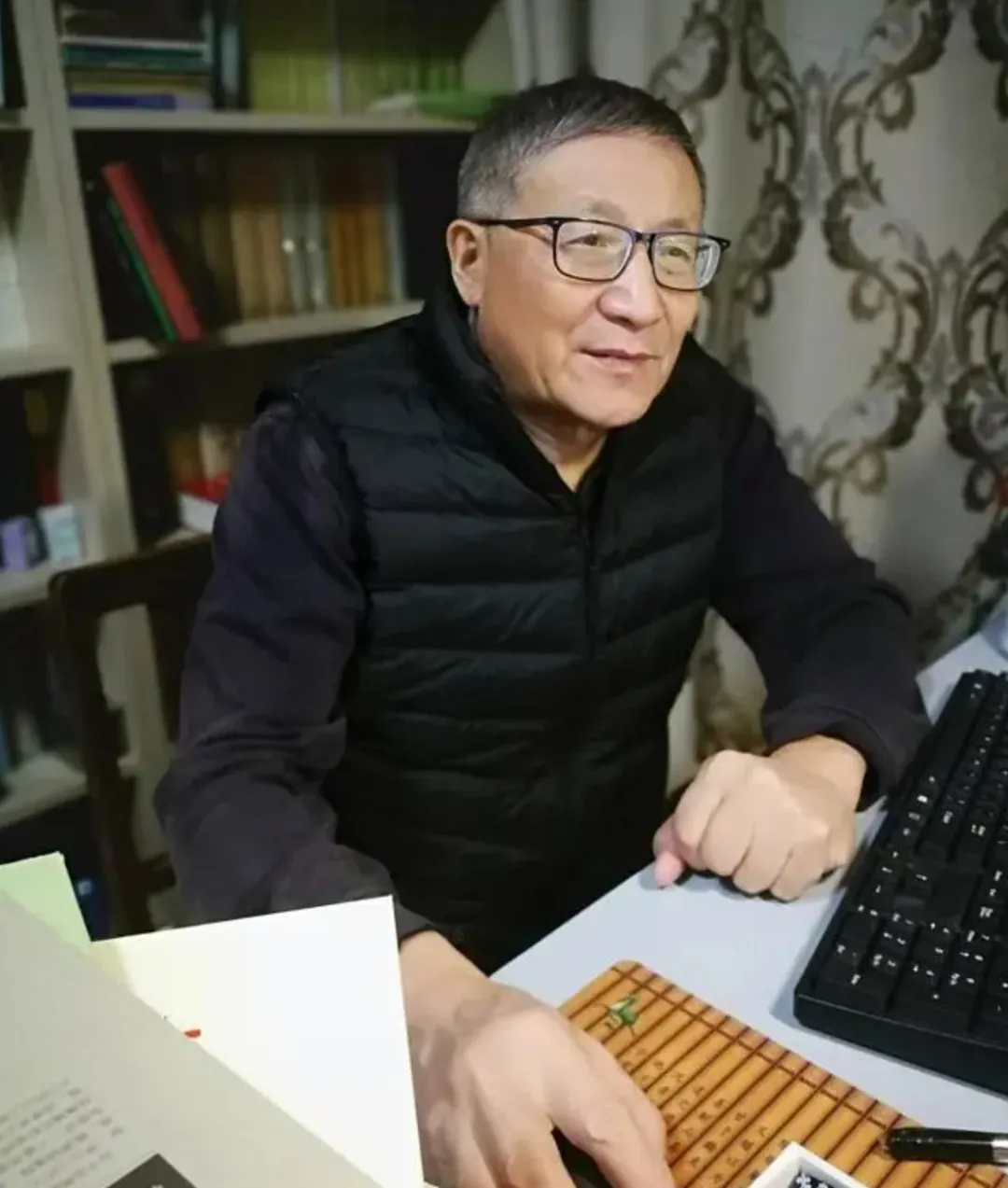
山林是大自然的不經(jīng)心之作,也為學(xué)問的生成和積累準(zhǔn)備了異樣的條件。曾經(jīng)在寶雞山區(qū)插隊三年的經(jīng)歷,使得我們對山野環(huán)境有著天然的親近。和古代許多詠唱山林優(yōu)美環(huán)境的隱逸者不同,我們是作為底層勞動者體驗這種生存條件的。作為農(nóng)人的勞動生活,有利于后來的史學(xué)研究者對古代農(nóng)耕經(jīng)濟的具體的理解。后來多次考察古代道路,以另一種身份走動于野山林路,又獲得交通史的新知。
承張慶捷、趙瑞民、郎保利等好友引領(lǐng),我們曾經(jīng)來到山西平陸漢唐黃河棧道遺址,觀摩他們發(fā)現(xiàn)的古代棧道遺存。看到朋友們身著救生衣,乘小船逐浪的工作照,也聽聞講述,得知了交通考古的生死艱險。

記得1990年8月步行考察秦直道旬邑—黃陵路段,除了負(fù)重爬坡的異常勞累之外,烈日暴曬,虻群圍攻,走得異常艱苦。張在明等著《嶺壑無語——秦直道考古紀(jì)實》一文,錄有《興隆關(guān)懷舊》一詩:“昨看艾蒿店,今在興隆關(guān)。麻灣餓飯?zhí)帲粍e十八年。”附記:“十八年前的1990年8月,王子今、焦南峰、周蘇平、張在明四人步行調(diào)查秦直道時,曾在黑麻灣林業(yè)站乞食。”在一個林業(yè)工區(qū)“餓飯”“乞食”的囧途經(jīng)歷得以真實記述。
拙著《秦始皇直道考察與研究》“后記”中附有詩作:“古嶺曾經(jīng)馳帝車,秦皇存定四極初。意得一統(tǒng)各安宇,烹滅六王莫不服。直道長城謀進遠,遺詔太子費躊躇。鄜州皓月秋光凈,廣路關(guān)山無字書。”詩雖不工,歷史感覺是實在的。這是因為踏行在秦時路面,真切體會到當(dāng)時筑路工徒的功勛與苦難的緣故。時間雖然相隔久遠,空間則在相同位置。因張在明發(fā)掘富縣樺樹溝口直道遺跡得以面世的秦漢車轍與足跡遺存,當(dāng)時偶然存留在塵泥之中,現(xiàn)在則深深刻印在我們心里。
原文鏈接:https://mp.weixin.qq.com/s/hv0CPxII4l49VAOlcceogw